韩天衡《篆刻病印评改200例》选登
个人日记
不教一日闲过
| 此学弟刘建平君所作。作者以古玺式出之。其实,对于古玺的认识,许多初学者并未把握。以琐碎为高古是误区之一;以含混为朴茂是误区之二;以破烂为拙厚是误区之三;以轻率任意变动字形为生动有趣是误区之四;以用刀的浮躁不实为得金石气是误区之五……此印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的缺点。诸如,金文的书写不规范,如“不”字;再如“日”字与左侧的“闲”字拼合不妥当;如“过”字的处理太散漫松垮。当然作者也似乎发现了此印的一些短处,故以在印石“打点”的手法弥补之。然而,整体之失,文字之失,往往不是靠“做”印面即能挽救的,倒是往往有“欲盖弥彰”的反效果。 欲修改此印。一是要令其刀刻出的线条有结结实实的圆浑感;二是要令其在散漫松垮的章法里玩味到作者是以严谨心作游戏相;三是在刻完字的印面上“打点”,不可乱撒“胡椒面”,而是“用得其所”,使其产生艺术效应。此改稿虽不“打点”,似也无妨;四是对其四周边栏稍加调整,求得印文与印边的一致性。 |
仁者寿
此印用刀犀利而具力度,其不足处在刀法相对单调。此外,在把握字形态势上也还欠火候。
此印的用刀是参法了《天发神谶碑》的。严格地讲,有其意而乏其气、有其爽利而乏其堂皇,这与用刀时只注意于用刀角之力,而未开发出用刃与背有关。我对其“寿”字之右下直笔做了改动,似可纠其不足。
此印在章法上也犯了“合章”的禁忌,如“者”字之右下直笔与“寿”字之左下直笔雷同,应避免,故笔者在改稿时令此笔上缩。笔势虽上缩,反收笔短意长、涨力内敛之效。又,作者将“寿”字之下“口”作“V”状三角处理,这也是败笔。在大头大脑、气格壮伟的格局与结构里,突兀地出现“V”状三角,就会大煞风景,非但不伦不类,而且气格纤萎,对此也做了改动。此印改动至此,与原印相勘,自有其明显的高下。如果读者能体会到这一差别,那么,我还要有如下的提醒:其实从大处讲,我们也只是改动了“寿”字的二根直线和下面的一个“口”的形状、部位,足可看出每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是血脉相通的,万不可小视、不可轻视。治印者每讲大局、讲章法,而具体地还是要落实到一点一划的细心推敲上。故云一点欠安,全印皆失,绝非是一句危言耸听的空话。
会景楼
| “会景楼”属仿汉之作,然明显地有近人仿汉之习气,如以利刃在线条间细切即其一也。此印稳妥而近于呆板,原因在于: 一、字的配篆过于机械地作横平竖直的堆砌。换言之,作者在配篆时完全排斥了感性和热情,而感性和热情较之理性往往更近于抒发艺心。 二、在配篆时,忽视了留红(即空地)与字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。留红形状的太方正、太几何形,都会酿成形式上的呆板。 具体分析“会景楼”的留红: “会”字上方留两“三角形”,下方留一小“菱形”; “景”字下方留两小方形; “楼”字“娄”旁下方留一突出的长方形。细考此印留红,相互之间总的说来还是有交流的,与文字也是顾盼有情的。唯“娄”旁下方突出的长方形留红过于抢眼,与其它处留红欠协调,与全印文字也少和谐。据此,吾对此部分做了改动。此外,线条间太多的断点,非但不古拙,反而给人以眼花缭乱般的做作感,故也应填去大部分。 |
庚辰大吉
| 永久学弟治印。此即为铁线篆式,取法在吴、赵之间。以用刀论,作者息心静气,一刀不苟,是可取的。但依旧有其不足,主要反映在篆法上。 对篆刻有所实践者,都应该知道,篆法是有方有圆的,而且是宜方宜圆的。然而宜方宜圆的采用,或以方为主,方中寓圆;或以圆为主,圆中参方。从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古今印章上看,那些刻意方圆平均的印作,没有一方是成功的。我自己以前也曾尝试过方圆折衷并用的方案,每每也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可见,在篆法的构想上,总是要讲方圆的主次、轻重,这对章法来说,是太重要了。 讲了这些道理,我们再来剖析此印原作,大致可发现有两种缺陷: “庚”字篆法,大体为圆。“庚”字下方作饱满的篆法处理,与其左下方斜角的“吉”字少呼应,因“庚”字之大,反衬“吉”字之小(其实二字的占地是相等的,是视觉产生了大小的差别)。 “辰”字篆法基本为方,而与其馀三字缺少神情的交融。 因此,我对“庚”、“辰”两字做了篆法上的改动,且让“庚”字之上端与边栏分开(因原作与边栏形成的“三角区”,往往是章法上的忌讳),至此,全印效果或较原作为胜。 |
古调独弹
| 此印属写意印范畴。其实刻印,古来无“写意”之说,近年方有此论,姑且引用之。写意之印,无非是对“工笔”而言,但写意决非随意。写意之难,难在写神。要写神又当以精心为前提,把不动脑筋、随心所欲的横冲直撞,称之为“写意”,只能是对这一风格不负责任的贬低。基于这种认识所刻的印,也决称不上高妙的“写意”印。 以原作“古调独弹”四字论, “独”字在篆法上是与其馀三字少了关照, “独”字的篆法太流太荡,那些非圆非方的笔道,的是有不入调的孤独感。 基于此,笔者对“独”字的某些线条作了率直的纠正,遂使此“独”字,有孤雁归队的感觉。 由此,我还想发表两点意见:写意印的用刀不宜纤弱,而宜泼辣;不宜做作,而宜自然;不宜简单,而宜简练;不宜直露,而宜内敛,而要臻此境确非多年的磨练所办到的。我们如果去读一些吴昌硕中年的印作,或是去读一些魏晋印中的精品,相信会获得多多的启迪。另一点即是残蚀印面。印面是可以残蚀的,尤其在写意印里,这往往是必要的,是有其相得益彰的烘托作用的。写意印面的残蚀,当然不会是天成的,当是印人所为,但难在人为残蚀,又不能有人为的痕迹,不能有贴上去的造作,不能因破而造成破碎的局面。总之,要以“浑然天成”为高明。古人有云, “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”。“既雕既琢”是指人为的制作;“复归于朴”是指其最终当给人以一无经过人为制作的大朴不雕的艺术效果。千雕万琢的苦心经营,能赢得一如原始的大朴不雕,这才真正地体现出不凡印人的艺心和艺术啊! |
古调独弹改稿.
古木生天际
| 此小篆人印,而多参让翁法,原作右侧“古”、“生”两字形体太收缩,故左、右两侧欠和谐。改稿1将原作之失加以纠正,而“古”、“木”两字占地小于它字,全印欠匀落;改稿2纠正了前两稿之失,似得规中矩矣;作者继刻改稿3,此印好处在于全印四乎八稳,而较之改稿2又不免有太刻意之感。故改印,当改则改,遇善则止。改过了头,也会有蛇足之弊。 |
古木生天际原作.
古木生天际改一.
古木生天际改二
古木生天际改三.
欣逢盛世玉兔欢
| 作者夏宇老弟,取法似在汉砖..然此印推敲不够,故产生了几个症结: 一、文字太随意,或太松、太散,或太欹、太拗,全印缺乏完整的构思。 二、用刀太尖削,对许多线条的处理,皆表现为头方而粗,尾尖而露,习气太重,使大印缺少必要的沉雄。 三、在章法上,作者留出“玉”、“兔”二字下方的空间,但却是以两字的失去平衡为代价的,不见精彩。 要之,疏朗写意印,疏而不能散,能得其“意”,方见功力。故建议作者纠正上述几点失误而改刻,成改稿。两稿相较,后印则明显地好于前印。 |
欣逢盛世玉兔欢原作.
欣逢盛世玉兔欢改稿.
杏花春雨江南
| 作者此为取法汉玉印者,安排颇匀整,但尚有可改动处:其一,笔道要细瘦些,以合玉印基调:其二,从字与字的关系、留红(空间)的关系两方面考虑,可对“花”、“春”、“雨”的笔法略做变动。作者遂刻成第二印,较之原作,似当刮目相看。然线条似可再瘦一线,则印更雅逸见神矣。 |
杏花春雨江南原作.
杏花春雨江南改稿
汉印遗风
| 赵珊珊女弟作。此印参魏晋凿印及瓦甓文字意趣入印,总体尚可。然细部存在问题较多:从全印的协调上推敲, “风’’字因右笔太向左侧欹,字态失稳;“汉”字水旁上伸下插,少了合力,也减弱了与其馀三字的照应。故对这二字做了一些改动。此外,吾对原作的一些线条做了十七处微小的修正,以期全印达到“汉印遗风”的朴厚、古拙的效果。我不想再去一一赘述,请读者自己去寻觅、比较一番,看看笔者到底做了哪些改动,并感悟一下其作用,如何? |
汉印遗风原作
汉印遗风改稿
胡守文
| 此印之处理存着许多种的表现形式,我随意写出此印初稿,法在赵之谦、吴让之之间。然似觉太佻娆,故成改稿1,法近汉格,平稳而乏特色,故也弃而不取。再成改稿2,法近汉铸,然此三字之难,难在“文”字:以前三稿统观之,即可发现其与“守”字字型近乎雷同,不做调度心不甘,调度过大又觉突兀,易失和谐。考虑守文兄为肖代书家,用印以稳重、大气为宜,故将“文”字做朱文处理。而朱文“文”字点划之间距相当于白文线条的宽度,这样全印粗看为白文,细审则为朱白相问,落落大力,于细微处求变化,此亦汉人法也。遂作定稿。 |
胡守文初稿
胡守文改一.
胡守文改二
胡守文完稿.
巨鹿园
| “巨鹿园”印是稚柳师由沪上乌鲁木齐南路寓所迁至巨鹿路后所用馆阁印之一,吾偶以圆朱印式为之。 初稿出,不恶,然自忖太四平八稳,遂将“巨”字中笔左缩,似较初稿有致。 顺着“巨鹿园”一印的用刀,想再发表些心得:刻印艺术,或谓篆刻艺术,都还是离不开一个“刻”字。明清印人对“刻”字往往从两个极端作偏颇意见:轻视者,以为用刀是无足轻重的一环,只消能按照印文刻出字来即可;神化者,荒诞地渲染用刀十三法、十九法之类,神乎其神。这都是走极端。而拙以为“篆”是“刻”的前提,篆不佳,“刻”再好也无法弥补先天的不足;“刻”是“篆”的延伸,“刻”得好,则是锦上添花。“刻”得差,则篆得再好,也必然是佛头着粪。 |
流水能西
| 东坡有句:“流水能西”。水者,柔也;流者,势也逆向而流,显示着作者主观意志上逆潮流而行的顽强刚毅的本色。吾爱其句.遂借以治印。初稿.对“流”、“能”做阔且密的安排,“水”、“两”做窄长的安排,并取迥文法。 改稿l,初稿有经营之嫌,遂变思路,作三密一疏的章法。然,自觉平平而少慧心。 改稿2,又变一章法,“西”、“水”做横窄安排,似不一般。惜又现造作之痕。 改稿3,将“水’’字由横放改竖立,如此,在疏密对比中加强了空间块面的变化。 改稿4,前四稿立意在巧,故又做拙的章法处理。此稿四字宽松作老实相,好处是落落大方,坦坦荡荡。细究底里,此印已落人完白山人窠臼矣。 改稿5,翌日以前五稿做细笔处置,昧近于赵之谦。印大笔细,倘用刀欠醇,易陷于靡薄,不取。 07-1-16 11:00 上传 下载附件 (57.35 KB) 改稿6,数稿不安,置匣有日,前六稿短长互见,颇难自决,吾本着“一味随人,不如择善从己”之旨,决定对改稿3某些局部稍作完善,以为定稿。呜呼,前后一周,空走了一段“S”形的回头路,可知艺事之足以磨人也。 定稿,又数日,对改稿6也欠心安,又趋于初稿思路,而竖“西”字上方顶“流”字末笔,使其下坠之九笔有所制约,可纠前七稿之失。吾深知人无完人,金无足赤,章法亦无完法。吾辈诚如炼丹之士,力求其近纯而已。 其实,并不在于多发几个例子,而是在于认真学习这些已经上传的例子。 我大概花了一个星期,把该书中有代表性的案例挑出来,尽量兼顾了字形、配篆、章法和刀法等诸多实际应用的方面,应该算是面面俱到了。韩天衡老师自己创作《流水能西》一印时,前后更易七稿,大家可以从当中领悟到精益求精的努力。 有為書灋工作室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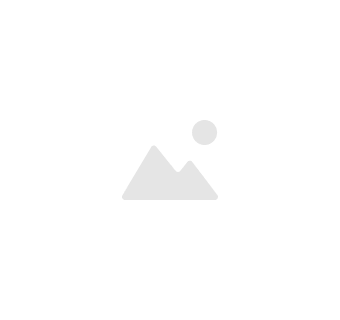 |
文章评论